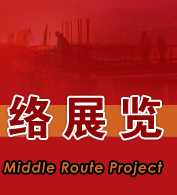我们作家诗人采风团是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而行,由北往南,直抵它的源头——丹江口水库。车过河北易县,我们见到了易水河,但不见河水,河床裸露如同戈壁滩,几头水牛在在河床中央,石砌的河堤横挂着标语。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忽然想到《渡易水歌》,荆轲至易水之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的精典画面,那萧萧易水呢,它们流逝到了何处?
我们站在河流中,河中没有了流水。在心中跳出这个句子。有河无水。整个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它们仅成一个名字,有其名没有了河水。干涸的北方,我们四处打听水的踪迹,它们流迁徙到了哪里,我这个从长江边长大的人,我的童年的家园被湖水包涵,到处是沟渠和清亮的河水,逐水而居,那是我们楚人的习俗。
现在,我知道我来到了北方,缺水的北方。国家在应对着环境的悄然演变,不得不把我们南方的水运送到北方来,这是一个国家重大工程:长江支流汉水上游丹江口水库的水通过人工明渠和隐藏的管道,经过豫鄂的伏牛山,过黄河、跨越漳河,经邯郸、邢台、保定进入北京市境。而我们采风队伍逆这条路线南行,见证这个时代人定胜天的工程。
人往南方走,水往北方流。我们人类在与自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争斗。改天换地,一个童年常出现的词语再次跳动在意识里,确实我们人类在与天斗与地斗,为了我们生存必须的水水水。何处有水的踪影,车过黄河,我们看见了水渐渐多起来,水池,绿树,油菜花,而我们见到水,那是惊心动魄的水,被污染了的水。死水。每每坐火车到苏州,火车进入无锡苏州境内,散落的工厂,在我面前穿梭而过的黑水。我们要什么GDP,但我们须臾离弃的不得的干净水源。四处是让人气馁的令人不安的现实,北方的干涸,南方河流的污染,南水北调的东线只有污水可调。所以我们沿南水北调中线赶赴丹江口长江的支流,南水北调工程的起点,是那样的关心着我们的水源。
河南温县孤柏山,我们看见了黄河,南水北调中线的控制性工程:穿黄工程就在这里,从长江迁徙过来的水要在这里与黄河里相遇,水从这里运往北方,从黄河南岸输送到黄河北岸,南方的水从这里从黄河底下的隧道穿过,我们看见了深深的圆筒结构的竖井,用一种进口的盾构机开掘隧道,它的盾体、刀盘、拼装机、传送机,泥水循环系统、人闸、网络系统;这个人造的庞然大物,它就要代理我们在地下落实我们的意志,就要穿空自然的黄河。盾构机迎接不同的地质结构,在掘进过程中刀具的磨损、可能遭遇古树和孤石的风险,它掘进的姿态,它所面临的挖面压力,这都成了我们关心的东西,还有它使用的期限,南方的水是否如期通过,一百年之后,我们几代人死了之后,它的状态又如何?面对理性的高科技,我们艺术家们有着人性的质疑。一个令人难堪的处境:为了满足我们基本的水的需要,我们付出了惊人的代价。我们有着的人的智慧但面对超越时空的质疑,我们也无法回答这样的发问。
我们这些在语言世界里思考的人类命运的人,这群“还自然之魅”的支持者,他们穿行在多种的时空里,审视着语言之外的世界我们人类的作为、制造出来的机器,这也不妨碍我们与那些在工程现场劳作着的人们的交流和沟通,他们戴过的红色头盔被我们戴上,他们在从事它们短促一生中的伟大事业,他们参与了一个时代的重大工程,见证了水的迁徙,而我们戴着头盔和他们在一起,关心着水的迁徙,和他们短时间地在一起,呼吸和感知,一个人渺小与超过自身局限的伟大。
在丹江口大坝的加高现场,我们听着技术人员的讲解,运输水泥桨的卡车在起起落,悬空的脚手架,那挥动小红旗的中年妇女,在蓝光闪现电焊光面前俯身的电焊工,我记住了他们一闪而现的面影。
在即将完工的南水北调水源工程的大坝上,观望那从汉江和丹江水汇合在一起的水库,这就是源头,这里的水要加高的大坝运往南方,一直到北京团城湖,一路供养沿线的北方人民。我站在那里遥望汉江,那是故乡熟悉的河水,它们部分人为地运往北方,南水北调,成了一个活生生词,它们契入了我的身体之中。水源。来自于我故乡的河水。俯身在大坝的清亮的河水面前,掬了一把,含在口里,南方的家乡的水,它们就要从这里出发,经过那迢遥的路程,经过它们不知道山涧,明渠,涵管,渡漕,过黄河、漳河、滹沱河、永定河到达京城。当我在寄居的北方见到它们,我在心里说,那是我们南方的水,它滋养了那里的人们和植物。它们和我一样完成了它自己的迁徙,一路经历了意想不道的路程和事物,在我们人类的挟持下一路走得那么艰难,身不由已的南方的水然后在干涸北方消散,但它会在另一场雨水中在云天之中回到它们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