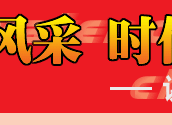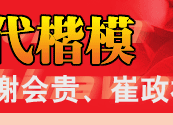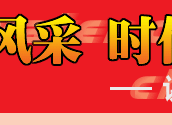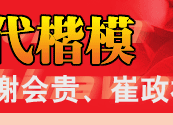2006年12月12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劳动者之歌》栏目播发了一位叫谢会贵的黄河水文人的事迹,节目播出后,在大河上下引起了热烈反响。随后,黄委发出“嘉奖令”,号召全河开展向谢会贵同志学习,授予谢会贵同志“黄河劳动模范”光荣称号,并组织“谢会贵事迹报告团”,在黄河系统进行了巡回演讲,在大河上下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一位普普通通、默默无闻的平凡看水人,为何能有如此巨大的时代感召力和撼动人心的精神境界呢?
人生选择
1957年1月,谢会贵生于青海省贵南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生活环境的落后和家庭的贫困,从小就陶冶了谢会贵诚实憨厚、吃苦耐劳的性格。
1975年7月,年满18岁的谢会贵离别青海高原,来到中原大地的河南开封黄河水利学校学习。从一名贫寒的农家子弟成为国家的中专学生,谢会贵十分珍惜良好的学习机会和生活环境,刻苦学习,勤奋读书。
1977年7月,两年学业很快便结束了,此时,摆在谢会贵的第一次人生抉择就是:留在生活和工作条件优越的中原;还是奔赴艰苦落后的青海。当时,学校天天不断地宣传,大喇叭里不停地播放着充满激情的动员讲话,号召同学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校领导也在大会上反复地讲:同学们,你们接受了贫下中农再教育,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现在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祖国百废待新,祖国需要你们,黄河需要你们,未来需要你们!你们应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好男儿志在千里!
谢会贵彻夜难眠,无数此的犹豫,好不容易离开艰苦的大西北,再回去不是太傻了吗?而且,在七十年代中期,中专生也算的上一名知识分子,并且完全有条件留在条件优越的地方工作。谢会贵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甚至是影响自己一生的关键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给学校革委会写了一封信,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随后,他的意愿很快如愿以偿,谢会贵被分配到了地处黄河源区的黄河沿水文站,这也正是黄河上最遥远、最艰苦的水文站。
黄河沿水文站建站于1955年6月,位于青藏高原青海省玛多县境内,站址海拔4200多米,是黄河流域海拔最高的水文站。水文站距省城西宁500公里,距黄河发源地270公里,区间有星宿海、扎陵湖、鄂陵湖等重要湖泊和湿地,是黄河源头地区的重要控制站,承担黄河源水文观测的艰巨重任,被人们称为“万里黄河第一站”。
1982年,实行水文“站队结合”,黄河沿水文站被更名为玛多水文巡测分队(下称玛多巡测队)。1987年,增设鄂陵湖、黄河乡两处水文观测站,测量任务统归玛多巡测队承担。
谢会贵来到玛多,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这里,成为黄河源头地区的水文工作骨干。
扎根河源
黄河源区流域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黄河每年总水量的40%来自这一区域,而且含沙量很低,水质很好,有“黄河水塔”的美誉,是黄河水量的重要来源区,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水资源地位。源区共有十几个水文站,海拔都在3000米以上。黄河沿水文站在这些水文站里也数得上最艰苦得测站。有位记采访黄河上游水文站后这样说: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是水利,水利行业最艰苦的地方在黄河上,黄河上最艰苦的是水文,水文最艰苦的是上游,上游最艰苦的地方在源区,源区最艰苦的要数玛多。
玛多地区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源头终年积雪不化,观测到的最低气温达摄氏零下53度,多年平均气温零下4.1度,全年没有无霜期。源区空气稀薄,含氧量只有内地的60%,初上高原,人们到玛多后的第一感受就是呼吸困难,心跳加速,在内地心跳每分钟七八十次,在这里可以达到一百多次,有些人心跳速率高达140多次,心似乎要从胸膛蹦出来。嘴唇干裂,浑身酸软,走路抬腿,就像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头疼脑胀,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有人戏称这就是《西游记》里紧箍咒的味道!
要长期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遇到的困难,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这里除了低矮耐寒的野草外,什么植物也不生长,栽不活树,种不成菜。有时从西宁运来一点新鲜蔬菜,到这里就冻坏腐烂了,因而价格昂贵。由于气压低,水烧到摄氏80度便开锅了,做出的饭半生半熟。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在这样折磨人的地方设立水文站,难道在海拔低一点的地方建站不可以吗?是的,我们的专家、领导想到了这个问题,可是没有好的办法,因为治黄事业需要。大家知道,黄河源区被称为“黄河水塔”,而源区的扎陵湖、鄂陵湖两大湖泊的水文变化是水塔的情雨表,所以我们必须在它的出口建站观测,掌握两湖水情变化规律,为黄河源区的开发与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正如为什么要在南极建立观测站一样。
谢会贵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在黄河源区,一干就是三十年,三十年守定黄河,守定水文,机械地重复着一件平凡得事业,流失的岁月在他脸上越来越多地留下了沧桑的印痕。
凡是接触过或了解谢会贵的人,都认为他不善言谈,憨厚朴实,对工作有一种忘我的执着。他在玛多三十年,经受的精神和身心的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他的家庭遭遇变故,体质越来越差时,上级领导几次动员他换一个环境,他却婉言谢绝,同事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却一直坚守在玛多。
谢会贵同志全身心投入黄河水文事业,工作中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在极度艰苦的工作环境中,长期忍受身体、精神上的艰辛磨难。他自1977年来到玛多水文站后,在大气含氧量仅有60%的高寒缺氧、临界生命禁区的玛多高原,历尽艰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遇到家庭变故、忍受妻离子散的人生巨大痛苦中,也没有为此而懊悔退缩影响工作,仍持之以恒地坚守在黄河源区水文测报岗位上。他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艰苦,坚持河源水文观测长达30年之久,和他的同事一道,观测积累了50多万组水文数据,为黄河源区水资源研究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科学数据,为黄河源区水文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谢会贵和他的同事们观测积累的水文数据,对黄河源区水文水资源研究利用,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黄河上游水电资源开发及水电枢纽调度运行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也是国家《水文年鉴》汇刊的基本数据。
甘于寂寞
谢会贵同志最为难能可贵的就是在艰苦环境中特别能忍耐。青海省倡导的“五个特别”高原精神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团结”。其中 “特别能忍耐”就是针对当地严酷的自然环境提出的。谢会贵在这方面,就是与地方藏汉干部相比,也可以说做出了典范。
一般人去玛多住几天,根本无法忍受高原反应带来的巨大痛苦,头痛脑涨,心跳气喘,饮食无常,彻夜难免。在该地长期生活会导致心肺肿大,对身体肌能造成严重伤害。玛多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张九奇说:“玛多县城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县城,高寒缺氧,四季寒冷,工作和生存环境十分艰苦,青海当地干部都不愿来玛多工作。由于环境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当地人均寿命仅为54岁左右。在玛多长期工作后,都会对人体造成无法恢复的严重伤害,离开玛多下高原后,也会变成长期吃药的‘药罐子’,当地流传说,在玛多工作是‘四十岁前拿命换钱,四十岁后拿钱保命’。地方干部也极少有在玛多工作30年的,一般干够20年就可以轮换或退养了。谢会贵在玛多工作长达30年之久,而且干的是更为艰苦的野外水文工作,的确让人佩服和敬重,对他的肯定和宣传,对我们地方干部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激励。”
黄河水文本身就是一个艰苦特殊的行业,也是黄河上最艰苦的岗位,在源区玛多坚持干水文,又是黄河水文系统最艰苦的工作。河源地区自然环境十分恶劣,最典型的特征为高寒缺氧。水烧不开,饭做不熟,而且常年吃不到新鲜蔬菜。火炉常年不灭,夏天也离不开棉衣,天冷时晚上睡在床上,褥子却冻结在床板上。环境艰苦,生活寂寞。在这样的环境中,谢会贵还要常年打冰、下水测量,有时头痛脑热,身体不适,但他强忍痛苦,从未耽误过工作。
1989年春节,谢会贵和同事卡文明坚守在离玛多60多公里的鄂陵湖水文站。四周方圆,空旷荒寂,无路、无电、不通邮,晚上点蜡烛照明,百十平方公里内没有一点人烟气息。大年三十这天下午,他俩从鄂陵湖打冰测流回来,脱下厚重的皮大衣和冰冻的棉皮靴,这时才想到该过年了!眼看太阳快要落山了,回玛多采购年货的同事因大雪封山无法返回。 “每逢佳节倍思亲”。此时此刻,年迈的父母,贤惠的妻子,娇小的儿女,无不令他们倍加牵挂。在内地,过年是非常热闹的事,可眼前,别说感受丝毫的热闹气氛,就是想吃顿饺子或像样的年饭也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奢求。他俩寂寞无奈,相对无言,斟满酒杯,遥望远方,默默向亲人祝福。不觉中,两人紧紧拥抱,放声大哭,难熬的大年三十,就这样在空旷的无人区和悲怆的哭声中度过。大年初一一大早,两人相对一笑,依旧去鄂凌湖上看水位、测流量。
谢会贵在鄂陵湖工作期间,一次和同事在湖面上刚测完流,漫天风雪骤然而至,他们迷失了回站的方向。正当在冰面上盲目地寻找归途时,猛然听到脚下响起令人魂飞魄散的冰裂声,好在年轻灵活,反应快,急速后退了数米,才算躲过一场灭顶之灾。若稍有迟疑,便命归黄泉了,那冰面下就是几十米深的冰水。
由于生活寂寞,谢会贵喜欢喝酒吸烟,但他并不悲观,而且很热爱生活,每年天暖时,他都要把平常采集的草籽撒到水文站的小院里,让自己生活的环境长出生命的绿色。
吃苦耐劳
谢会贵并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默默无闻,兢兢业业,甘于吃苦。也正是在这种平凡枯燥、艰苦寂寞,日复一日的辛勤工作中,显现出了谢会贵同志的可贵之处,他把平凡普通的艰苦劳作升华成了一种高尚和伟大的精神。
谢会贵在工作中从不讲价钱,累活、苦活总是抢在先,下水、打冰也总是比别人付出的艰辛更多。在高寒缺氧地区,从事水文野外作业非常艰苦,打一个冰孔、测一份流量要比内地多付出数倍的气力,打一个一米多厚的冰孔就需要两个小时左右。一般人打一个冰孔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了,但谢会贵一鼓作气等连续打两到三个冰孔,每次测流都是他打的冰孔最多。土生土长在青海、与谢会贵长期工作的藏族同事卡文明说:“我和谢会贵同干了四年,他工作认真积极,我最佩服他打冰孔,测一次流量要打十几个冰孔,我们打一个就心跳气喘不行了,谢会贵却能打两三个。”
1978年,因为谢会贵年轻、适应性强、能吃苦,被选拔参加了黄河西线南水北调考察。考察中, 7月27日、8月6日两天,同时对黄河源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两条源头支流分别进行了流量实测,为确定黄河正源和南水北调西线引水线路提供了重要资料。测流中,谢会贵的任务就是下水测流。源头的河水大多来自冰山融水,寒冷刺骨,一次流量测下来,双腿便被冻的红肿麻木。谢会贵测得的流量成果已被载入历史,成为珍贵的源区第一手水文资料。
1979年冬,上级给黄河沿水文站下达了冰期试验任务。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寒缺氧地区,要完成这项任务,艰苦程度可想而知。谢会贵是这次试验的骨干,说是骨干,其实就是出苦力、打冰孔。冬日的黄河,河面冰厚可达一米多,铺天盖地的积雪也有一米多深。别说作业,抬腿走路都非常吃力,而每次测流时,还要在坚硬冰面上首先打出十几个冰孔,然后才能下仪器测流量。冰期试验要在规定的时期内,不分昼夜,每六个小时测一次流。
这年冬天,谢会贵和同事们在摄氏零下40多度的低温下,一共测了40多份流量。谢会贵也因此得一个外号:“玛多打冰机” !说到打冰,是一件极其艰苦的差使,在高寒缺氧情况下,一般人空手行走都十分困难,要挥动几十斤重的钢钎,竭尽全力,打到一米多厚的冰层上,只留下几道浅浅的印痕,有时用力过猛还会摔个大跟头。在黄河源头干水文,打冰下水是家常便饭,天长日久,年年如此。多少年来,每次测流,谢会贵都是抢先打冰,抢先下水。近年来,谢会贵年龄越来越大,气力渐渐衰退,身体也落下很多毛病,常年不敢脱掉棉裤,始终穿着妻子给他做的狗皮护膝。但他仍然保持多年来的工作习惯,打冰下水、吃苦出力的事,还总是抢在前面。
忠诚负责
有人恰如其分地把水文测报比作是“良心活”,事实的确如此。在远离人群,无人监督的荒原僻野,谢会贵对工作高度负责,一丝不苟。无论白天黑夜,风狂雨猛,谢会贵都要严格按照操作程序认真作业。一次,因人力不足,玛多当地一位熟人被谢会贵请去帮助测流,当时风雨很大,熟人对谢会贵说,这么认真干什么?你测的数字粗一点谁能知道!谢会贵马上严肃地说,这可不能马虎,差一点点都不行!30年来,谢会贵经手测过的流量单次质量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观测积累的水文数据均满足规范要求,玛多水文站的水文资料整编成果全部达到验收水平。
上世纪90年代初期,玛多水文巡测分队成立后,负责鄂陵湖、黄河沿、黄河乡三处水文站点的监测工作,谢会贵又承担起开巡测车、打冰测量双重重任,为单位节约了大笔开支,虽然家庭生活还很困难,但他自己却从没有领过一次出车补贴,也从未申领过一次困难补助。
2003年,由于在高寒缺氧的艰苦高原长期生活,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谢会贵突发脑血栓,西宁水文局安排他住院治疗,住院没多长时间,当单位领导去医院看望他时,发现谢会贵不见踪影,连忙打听后才知道他已跑回了玛多。原来,长期吃苦忙碌习惯的谢会贵反倒不适应安逸闲适的生活,整天想着玛多和他的工作,没等病情痊愈,便悄悄回了玛多。长期的高原生活,已经把谢会贵和高原、黄河水文融为了一体。
在玛多工作30年的谢会贵至今仍有严重的高原反应,有时甚至比初上高原的人反应还要强烈。现在,年逾50岁的谢会贵每次从西宁到玛多后,依旧头痛脑胀、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每次都要经过十天半月的痛苦折磨才能逐渐适应。
舍家为业
1979年,谢会贵在海拔4200多米的高原与玛多县民贸公司一位女工结了婚。1984年,谢会贵当了爸爸,随着儿子渐渐长大,夫妇才意识到孩子需要好些的学习条件。他感到很愧疚。妻子想在西宁安个家的希望谢会贵也一直无法实现。
1992年,妻子与他离婚离开了玛多。妻子带走了大儿子,一岁的小儿子留给了谢会贵。谢会贵既当爹、又当妈,还要工作,生活虽然季度极度艰辛,但他却从没因此而影响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谢会贵把小儿子送回老家让姐姐照顾。朋友劝他说:“老谢呀,你就是回西宁卖冰棍,再没本事给人家擦皮鞋,也比在这鬼地方强!总可以照顾孩子生活和学习呀!”谢会贵很固执,根本没有考虑要离开玛多。
当地干部有轮换制度,而12万多平方公里的水文监测区域,仅有十几个水文站,每个站平均只有三到四名职工坚守,一个人要顶几个岗位,谁要离开,就会出现空缺。因此,谢会贵和他的同事无缘享受轮换的待遇。
国家没有忘记他们,水利部、黄委会等各级领导没有忘记他们。后来,在青海西宁市建起了水文职工生活基地,黄河源区的水文职工都在西宁分了房子,解决了后顾之忧。
1994年,朋友们帮他在西宁介绍了一位女友,当女友了解到他的经历后,看他为人朴实忠厚,在玛多又受了那么多的罪,很同情他,就嫁给了他,谢会贵才算在西宁有了新的家。有了新家,少了后顾之忧,谢会贵依旧常年坚守在玛多高原,守定他热爱的黄河,工作也更加投入了。
每当说起西宁,谢会贵脸上都流露出满意的笑容。谢会贵说现在好多了,比起牺牲在河源的水文先辈,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能在西宁有个家,我们从前想都不敢想。
然而,世间的事物都有两重性。利弊同在,福祸相依。谢会贵在西宁安家后,工作地却无法变动,因此,只能侧重一方。由于工作原因,谢会贵仍要常年坚守在黄河源头玛多水文站,常常一去就是几个月甚至大半年,而每次回家,呆不了多久,就得赶回水文站。每次与妻子儿女见面都是来去匆匆。
谢会贵的女儿谢婷婷说:每当周末,看到别的孩子由父母陪着逛公园、逛商场时,我就特别羡慕,说心里话也有点怨恨爸爸。一次我问爸爸:咱全家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呢?爸爸看看我,笑笑说:会的,会的。我一次次满心欢喜,却一次次失望落泪。多少次看见妈妈独自出神发愣,伤心难过;多少次看见妈妈暗自伤心落泪,希望有人来扶她一把!妈妈说,黄河是你爸爸的命,他守着河,才心安。
提起工作,谢会贵对家人总是轻描淡写,很少讲他的艰辛和苦寂。给他们说的最多就是草原的辽阔和黄河的美丽。妻子一直想去玛多看看他工作的环境,可是谢会贵知道她有气管炎,身体也不太好,去高寒缺氧的高原是非常危险的,一直都没有同意。当电视里播出谢会贵工作的画面后,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才知道,谢会贵不但要在黄河上打冰,而且还经常下水测流,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轻松,也才知道谢会贵有个外号叫“玛多打冰机”。
当时,与前妻离婚后的谢会贵带着大儿子住在玛多。谢会贵每天忙于工作,看水位,测流量,一忙就是大半天。夏天还好些,一到冬天,天气特别寒冷,每次去河边都要全副武装,周身除了眼睛外全包裹得严严实实。外面大雪扑面,寒风刺骨,路滑难走,往返一次就要好几个小时。
谢会贵的孩子印象最深的就是,爸爸布满冰凌的靴子。每次从黄河上测量回来,谢会贵的皮靴上都会冻上一层厚厚的冰甲,儿子经常帮他烘烤靴子。烧的是牛粪,热量不足,烤好长时间,靴子也不能完全干。第二天,谢会贵就穿起还没干透的靴子继续工作。常年累月,腿就落下了毛病,一年四季都不敢脱掉棉裤。妻子心疼,特地给他做了双狗皮护膝。只到现在,无论春夏秋冬,谢会贵都穿着妻子做的护膝。
三十年来,谢会贵遇到过很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艰辛和生活困难,但谢会贵认定,选择了水文,就选择了艰苦。他从内心知道,高寒缺氧,生活艰苦,没人愿意来这里受罪,但再艰苦也得有人坚守。考虑到谢会贵在玛多工作时间过长,单位领导曾多次考虑调换他到条件好一些水文站工作,但都被他直言谢绝。谢会贵说:“我在玛多时间长了,对当地情况熟悉,适应性也强一些,对这的工作和环境都很熟悉,工作起来也方便一些,换了别人照样要受罪,我就在玛多干吧,干到退休,哪也不去了。”
朴实无华
玛多县城很小,全城不足千人,从县城的一头到另一头用不了十分钟便可挨门串个遍,大家相互都很熟悉。生活中的谢会贵朴素诚实,为人正直,他喜欢给别人帮忙,人缘很好,在玛多县城,没有不认识谢会贵的。不论藏汉同胞,不论年龄大小,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阿爷”。一方面是因为他人缘好,待人厚道;另一方面则因为环境艰苦恶劣、生活艰苦,导致他过早谢顶显老的缘故。
谢会贵说,我的青春年华留在了玛多。其实,我们黄河源区水文职工就是一个群体,有十几个水文站,有几十位同事,他们虽然没有在一个站上像我这样干的时间长,但他们也在黄河源区的水文站转来转去。我的藏族同学卡文明,和我同一天到黄河源区,和我在玛多一块就呆了六七年,后来就在源区几个站转,一干也是三十年,靳振坤、刘国良、刘春孝等二十几名同事还在黄河源区坚守着,他们吃的苦不比我少,他们和我一样,我们干的工作很平凡,就是看黄河水,测流取沙看水位,只要吃苦耐劳、踏踏实实干就够了。
在突然而至的荣誉面前,谢会贵不骄不躁,平和自然,他认识到,上级关心可以改善工作条件,但永远也改变不了恶劣的自然环境,谁到那里都会高原反应,都会喝酒,都会抽烟,都会想家。黄河源区水文站离不开水文职工去坚守,我要继续努力,踏踏实实,干好工作,不辜负领导和大家的期望。
一个人的生命过程是短暂的,谢会贵把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艰苦的黄河水文事业。在他身上,集中体现了“献身、负责、求实”的水利精神,他的事迹为新时代的“劳动者之歌”加注了动人的音符!
来源:水利部网站 2007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