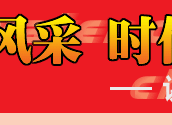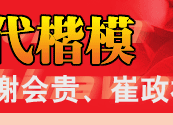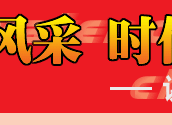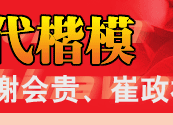平凡是什么呢?
平凡是一种境界。
大地平凡,你会惊于这平凡中的美丽;
季节平凡,你会发现这平凡中的永恒;
人生平凡,你会体味这平凡中的珍贵;
岗位平凡,你会懂得这平凡中的伟大。
——题记
玛多,藏语意为“黄河源头”,黄河从巴颜喀拉山北麓发源后,一路奔腾,在这里与人类第一次亲密接触。这里是黄河上游的第一个县城,有人这样描写玛多:蓝蓝的天上轻轻地飘着朵朵白云,绿绿的草地上牛羊悠闲地散步,河谷里散见牧民的帐篷,远山传来悠扬的牧歌儿,格桑花遍地开,一种远离尘世喧嚣的宁静……
可是又有谁知道,这里平均海拔4200米,没有树木能在这里存活;这里高度缺氧,只有平原含氧量的40%,头痛气短是初来高原时的身体反应;这里气候恶劣,平均气温零下4.1摄氏度,一年四季毛衣毛裤都是生活必备……的确,与其说这里远离尘世喧嚣,不如说与世隔绝;与其说这里美丽宁静,不如说这里荒凉冷清。
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有一名水文人,从他年少青春时开始,到如今的步履蹒跚,默默地守着静静流淌的母亲河,三十年如一日,没有人知道他的艰辛、他的寂寞,只有黄河知道他为治河事业积累的宝贵基础资料、为水利事业的无私奉献。
只有黄河能为他作证。
他就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玛多水文站的职工谢会贵。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朴实的想法让他与高原结缘30年
在玛多,你要是问起一个叫“谢会贵”的人,知道的人也许不是很多,可是你要是提起一个叫谢光头的,那便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其实,谢光头就是谢会贵,他不是什么名人,只是在这个小小的玛多县城里像他这样待了30年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
30年前,谢会贵还是黄河水利学校的学生。那一年,是1977年,谢会贵的选择注定了他一生与黄河源、与玛多结下了不解情缘。
谢会贵是青海省贵南县人,1977年,就在毕业前夕,谢会贵向学校递交了决心书,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的梦想。“好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
要说谢会贵不了解玛多那是骗人,出生在青海的他对玛多的艰苦十分清楚。可是,“青海是我的家乡,我自己都不去,谁还会去呢?”就是这么简单的想法,年轻的小伙子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收拾好行李,怀着对青藏高原、对家乡的美好憧憬,从开封来到了西宁。
谢会贵在西宁等了8天,才等到了一班路过玛多的汽车。498公里,我们现在看来也不过5个小时的路程,而当时谢会贵却走了整整4天。
这是怎样的一个县城啊。尽管在来之前谢会贵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还是被眼前的一切弄迷糊了。当时的玛多县城灰突突的一片,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
“现在要是拍战争片可能最合适了”,他开玩笑地描述初见玛多时的惊讶。
“刚到玛多时真是不适应。”没有电、没有煤油灯,只能烧牛粪。开水永远只能烧到80摄氏度,米饭永远是夹生的……艰苦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高原反应带来的头痛欲裂、心慌胸闷、喘气困难,折磨得谢会贵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他突然很想家!难以克制地想家!
在玛多水文站坚守了多年的老站长,看着这个20岁、还有些单薄的小伙子,主动提出让他回家住些日子。但谢会贵在家住了不到20天,还是返回了水文站。“我是自愿到玛多来的,给学校的决心书也是自己主动递交的,我不能这样就打了退堂鼓。必须信守诺言,绝不能当逃兵。”就这样,年轻的谢会贵在这里留了下来,一晃就是30年。
事实上,谢会贵有很多机会可以离开玛多。1978年7月27日,谢会贵对黄河河源玛曲和卡日曲分别进行了测流,两条河流第一次有了同日测得的可比流量,而这些数据成了谁是黄河正源之争的宝贵资料。在考察过程中,考察队长董坚峰的坐骑突然受惊,当时,谢会贵正骑马与他同行,千钧一发之际,谢会贵眼疾手快,一跃用自己的马拦住董队长的马,并奋力死死挽住惊马的缰绳,避免了一次事故。考察结束时,董队长问谢会贵愿不愿到郑州工作。与缺氧的“世界屋脊”相比,四季分明、桃红柳绿的中原几乎就像天堂一样。但想到一年前交给学校的那份决心书,谢会贵谢绝了队长的好意。他不是不想到内地工作,而是他必须信守自己的诺言。
30年,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变成了“谢光头”。过早的谢顶让谢会贵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年纪轻轻就被玛多的孩子们叫做“老阿爷”。
高原苦,苦在难耐的寂寞
——他不惧怕高原反应的剧烈、物资匮乏,怕的是与世隔绝的无望与寂寞
黄河沿是玛多县城所在地,当时全县只有3000多人,而县城的机关职工、家属、驻军加起来也不过200人,全部建筑也不过是沿青康公路两侧的两排院落。水文站坐落在县城中央,院子里只有五间房子。
玛多的气温很低,每年有8个月的烤火期,实际上就是火炉长年不灭。即使是在夏天,早晚也离不开棉衣,三伏天有时候看来天气晴朗,一会儿刮上一阵风,便会下起雪或者冰雹来。这里风很大,刮起来真的可以用“飞沙走石”来形容。
从水文站到断面只有两公里多的路程,骑自行车用不了五分钟,早上8点定时观测。出发前,先穿好皮大衣、毡靴,戴上口罩、皮帽,扎好围巾,然后戴上烤热的皮手套,一出门就骑上自行车快速前进,走不到一半路,手就冻得麻木了。眉毛、口罩、帽檐上都结了厚厚的一层霜。
一间房生一个火炉,炉子周围一米内还感到有些热气,再远就不暖了,大家睡的是床板,铺的是毛毡和羊皮褥子,人睡在上面,褥子却冻结在床板上。
这里除了低矮耐寒的野草外,什么植物也没有,栽不活树,种不成菜。有时候从西宁运来一点蔬菜,到这里就腐烂了。于是冻白菜就成了谢会贵他们最常吃的蔬菜。把冰疙瘩一样的白菜先放在开水中焯,再放在凉水中拔,最后放在油里炒。这样几经折腾,菜中的营养成分早就被破坏殆尽,可是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在谢会贵眼中,高原的苦不是指高原反应的剧烈,也不是没有蔬菜的物资匮乏,而是与世隔绝的无望,不能与外界及时沟通信息的寂寞。精神生活的空白是几十年来最难忍受的。
有一年春天,谢会贵的母亲生病,作为老幺的谢会贵赶回家看望年迈的母亲。当他无意间看见家门口盛开的无名小花时,居然忍不住激动地流下了热泪。男儿有泪不轻弹,更何况谢会贵是高原上响当当的汉子。这些一般人都不会看在眼里的,连名字也叫不上来的小花,在谢会贵看来却是那么的娇美、那么的不寻常,因为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久没有看到如此缤纷绚丽的颜色,几乎快要忘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色彩。他的大儿子,出生在玛多,五六岁时,居然以为世界上的水果只有苹果。
在玛多,一个月才能看到一次报纸,上面的消息早已经成了“旧闻”,可是谢会贵和他的同事们依旧爱不释手。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就是水文站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工作条件、自然条件的艰苦我们都能克服,可是这最难耐的就是寂寞。”
谢会贵与同事卡文明在鄂陵湖过年的故事在黄河上游水文职工中流传很广:那年大年三十,去玛多采购年货的同事因大雪封山未能回来,没有团圆的饺子,也没有辞旧迎新的鞭炮,只有两条生羊腿。谢会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卡文明是黄河水文系统唯一的藏族同胞,理应受到更多的关照,可过年他连家都回不去,还得待在这没吃没喝荒无人烟的鬼地方。作为站上的负责人,谢会贵感到很对不起卡文明,两人一边吃着生羊肉蘸盐巴,一边喝着烧酒,谢会贵好言劝慰卡文明,劝着劝着,自己先哭了,然后两个汉子紧紧抱在一起放声大哭……
测流的艰辛铸就了“玛多打冰机”
——现代化的打冰机因为“缺氧”不能正常工作,扛着冰钎的谢会贵就成了玛多的“打冰机”
有人说,社会上最艰苦的行业之一是水利,水利行业最艰苦的地方在黄河,黄河上最艰苦的地方是黄河水文,水文最艰苦的是上游,上游最艰苦的地方在源区,源区最艰苦的地方在玛多。这里被称为生命禁区。
玛多水文站位于玛多县城边上,1955年6月建站,担负着黄河源头重要的测流任务,是黄河源头重要的水文站点之一。建站初期,曾有两名职工在测流时被匪徒枪杀。但是因为其作用的重要,尽管这里条件十分艰苦,水文人还是前赴后继地在这里坚守。
谢会贵在鄂陵湖工作期间,一次和同事在湖面上刚测流完毕,漫天风雪骤然而至,他们迷失了回站的方向。正当在冰面上盲目地寻找归途时,猛然听到脚下响起令人魂飞魄散的冰裂声,好在他们年轻灵活,反应快,急速后退了数米,才算躲过一场灭顶之灾。若稍有迟疑,便命归黄泉了。
1979年,万物复苏的春天,华夏大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水文站也开始搞“站队结合”。这年冬天,上级给这个站布置了新的测验任务——冰期试验。这项工作在内地做起来都十分困难,在海拔4200多米的黄河源区,其难度可想而知。
谢会贵是这次试验的骨干。所谓骨干就是凿冰孔,在那寒冷缺氧的环境中,抬腿走路都很吃力,他们还要在一米多厚的冰上凿出一溜冰洞,完成试验任务。所谓试验,简单地讲就是每小时测一次流量。
冬季测流是很费气力的。每次测流前打冰孔就要几个小时。用一个两米长、一二十斤重的冰钎,一下一下把一米多厚的冰层打透。由于高原缺氧,稍一出力就喘息不止,有力使不上。打冰孔本来很费力,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里,还要脱掉皮大衣,累得满头大汗。一次要打十几个冰孔,需要不停地工作两三个小时。回头去安装流速仪时,冰孔又冻结了一层冰,还要再打一遍,捞净冰块。放下流速仪前,要用热水把仪器的转子部分冲开,仪器才能正常运转。
河上坚冰厚达1.5米,铺天盖地的积雪也有一米多深,就在这种冰天雪地的恶劣环境中,就在那粗重的喘气声中,就在那一声声凿击冰面的锵锵声里,谢会贵和他的同事硬是凿一个冰孔喘半天气地完成了冰期流量试验。“玛多打冰机”的头衔就这样落到了他的头上。
30年,玛多水文站仅站长就换了七八任了,谢会贵成了这里名副其实的老同志了。可是,每次打冰测流,谢会贵依旧会穿着胶皮裤冲在最前面,一点也不服老,每年仅穿坏的胶皮裤就有三四条。现在玛多水文站的站长梁海青十分钦佩这位“老同志”。“别看老谢是这里资历最老的职工,可是干活一点不含糊。投入又吃苦。外业测验总是抢着下水,让别人作记录。”
谢会贵这样向我们解释他抢着下去测流的原因:“我在这里待了30年了,已经基本掌握了这段河床的变化规律,遇到危险情况可以及时应对,让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下去,我还真不放心!”
其实,这正是将危险留给了自己。1991年1月,谢会贵和同事林伟如往常一样到断面测流,为了将仪器深入河底,谢会贵穿着胶皮裤跳入了冰冷的河水中。这是玛多历史上最低气温的一个月,零下54摄氏度。正当谢会贵全神贯注地忙碌着的时候,一股暗流将它冲倒,等同事将谢会贵从河里捞上来的时候,他早已全身冻僵,成了“冰棍”。就是这样,在第二天的测流中,谢会贵又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
同时,谢会贵还是水文站的兼职司机。巡测的时候必须出车,玛多水文站负责的另两个断面,分别距玛多60多公里。这60公里路可不是我们想象的路段,这里路况不好,陷车是常事,而且荒无人烟,修车时想找个石头支一下都很困难,发动机也是动不动就想休息。这时候,谢会贵总是脱下大衣,用自己的胸膛温暖发动机,再把衣服放在车轮下,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罢工的汽车从里面拽出来。有一次,谢会贵和同事刘玉平从热曲断面测流完毕,已是下午6点。在返回玛多的途中,汽车坏在了据黄河乡20公里的地方,修了几个小时,连测流时穿的救生衣都垫上了,一连折腾了几个小时,4个人又沿原路将车子推回了黄河乡,在冰天雪地里折腾了整整一夜。
作为兼职司机,他开过手扶拖拉机、摩托车、解放牌卡车、跃进客货两用车、北京吉普、切诺基到如今的皮卡,经他手开坏的车也总有七八辆了。跑过的路更是不知有多少公里,可是谢会贵愣是一天的出车补助也没有领过,开车、测流,一人干两个人的活丝毫没有怨言。
玛多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张九奇说:“玛多县城是青海省海拔最高的县城,高寒缺氧,四季寒冷,工作和生存环境十分艰苦,青海当地干部都不愿来玛多工作。由于环境给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威胁,当地人均寿命仅为54岁左右。在玛多长期工作后,都会对人体造成无法恢复的严重伤害,离开玛多下高原后,也会变成长期吃药的“药罐子”。当地人都说,在玛多工作是“40岁前拿命换钱,40岁后拿钱保命”。地方干部也极少有在玛多工作30年的,一般干够20年就可以轮换或退养了。谢会贵在玛多工作长达30年之久,而且干的是更为艰苦的野外水文工作,的确让人佩服和敬重。
西宁市里的“寻人”事件
——就在西宁市人仰马翻地寻找从医院失踪的人时,一辆开往玛多的长途车正载着谢会贵奔向他多日未见的黄河
西宁水文勘测局的领导知道水文职工在高原缺氧地区的艰辛,也多次提出要将谢会贵调到山下条件好些的水文站去。可是已经将自己的生命与高原融为一体的谢会贵却这样告诉领导:“这里虽然艰苦,可是环境我早已适应了,情况也熟悉。反正工作总是要有人来做,换其他同志来吃苦,还不如我继续在这里干。”
长期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工作,是对人意志的考验,但也确实是对人身体的摧残。30年,小谢变成了老谢,“玛多打冰机”经过了30年的磨损也老化了。谢会贵的身体已不如年轻时候,关节痛、胃痛,这些在长期高寒缺氧地区工作带来的疾病,一刻不停地折磨着他。
2003年,由于在高寒缺氧的艰苦高原长期生活,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谢会贵突发脑血栓,已经认不得人了,情况十分危险。西宁水文局安排他在西宁住院治疗,领导这样盘算着:这次下来就不让老谢再上去了,找机会好好做做工作,给他在西宁找个轻闲点的工作,毕竟老谢年纪也不小了。可是住院没多长时间,当领导去医院看望谢会贵的时候,发现他居然不见了踪影。
而正当西宁人仰马翻地寻找“失踪”的谢会贵的时候,这场寻人事件的主角却正坐在开往玛多的汽车上,奔向他多日未见的雪山、许久未能亲近的母亲河。“要是我在西宁,那我就废了,离开了水文站,我什么都做不了。”谢会贵这样解释他偷偷溜回去的原因。
值得欣慰的是,在上级关怀下,源区水文测报技术升级项目正在建设,其目标就是用现代科技手段,使源区水文测报走向现代化,由驻守变为巡测,由巡测变为无人值守,把水文职工从艰苦的环境中解放出来,但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这里的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
“内秀”的水文人
——与自然亲近使他朴实无华,心灵清澈见底
水文事业与社会的接触比较少,水文人也不被人认识。了解他们的人会说他们与自然亲近,有着由内往外的朴实,不了解的则会说他们缺少生活的情趣,在荒山野岭待傻了。
而谢会贵就是为了他热爱的黄河,忍受了别人的不解,忍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
有人说谢会贵很不幸,因为执著于水文,他的第一个家庭破碎了;也有人说谢会贵很幸运,正是他的这份执著和朴实,为他迎来了现在幸福美满的家庭。
当年,年轻英俊的水文职工谢会贵在高原上找到了自己的幸福:与玛多县民贸公司的出纳员在雪域高原和黄河的祝福下结为夫妻。而他们的大儿子也在1984年呱呱坠地了。
随着孩子的慢慢长大,他们才逐渐意识到不能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因为当别人的孩子每天忙于上各种辅导班,学习钢琴、舞蹈、计算机的时候,他们的孩子还惊异于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除了苹果之外的水果。如果孩子在这里长大,就废掉了。孩子需要学习,需要开阔眼界,需要和外面的世界接触。
1980年,水文工作实行了站队结合改革,成立了西宁水文勘测局,目的就是为基层一线职工建设生活基地,解决后顾之忧。
妻子想在西宁安个家的希望,谢会贵一直无法实现。无奈之下,1992年,妻子与他离婚,离开了玛多。
离婚的那天晚上,谢会贵喝了很多酒,边喝边唱着《沙娃泪》,他舍不得妻子的离开,可是也尊重妻子的选择,毕竟他要扎根的是男人都不愿意留下来的玛多啊。
妻子带走了大儿子,一岁的小儿子留给了谢会贵。谢会贵既当爹、又当妈,还要工作,生活虽然极度艰辛,但他却从没因此而影响工作。为了不耽误工作,谢会贵把小儿子送回老家让姐姐照顾。朋友劝他说:“老谢呀,你就是再没本事,回西宁卖冰棍,给人家擦皮鞋,也比在这鬼地方强!起码可以照顾孩子生活和学习呀!”谢会贵很固执,根本没有考虑要离开玛多。
善良的人总是会受到命运的眷顾。1994年,朋友们帮他在西宁介绍了一位女友,当女友了解到他的经历后,看他为人朴实忠厚,在玛多又受了那么多的罪,很同情他,就嫁给了他。这样,谢会贵才算在西宁重新有了一个家。有了新家,少了后顾之忧,谢会贵依旧长年坚守在玛多高原,守定他热爱的黄河,工作也更加投入了。
谢会贵的妻子说他能在家待的时间不长,现在条件好了,冬季实行了巡测,谢会贵才能在家多呆几天,平时几个月也难得回来一次。
幸福得来不易,谢会贵也异常地珍惜。谢会贵抽烟很凶,尤其是在酒后,最多的时候一晚上抽过五六包。家人、同事都多次好言相劝。可是长年一个人在玛多,打发寂寞的方法除了抽烟喝酒,谢回贵再想不起还有什么了。然而,妻子有气管炎,所以在家的时候,谢会贵总会克制自己,不抽烟喝酒,尽心尽意地呵护着这份小幸福。
而妻子也心疼谢会贵为支撑这个家所付出的一切。家里大大小小的罐子里,不是给谢会贵治疗胃病的,就是治疗风湿的。
这是一份默契,也是一种甜蜜。
谢会贵是热爱生活的,也充满生活的情趣。
就在树都不长的玛多,每年天气转暖的时候,他都会拿出平常收集的草籽精心地撒在水文站的小院里,使荒芜的院落渐渐有了生命的绿色。看着那绿油油的披肩穗一天天茁壮成长,谢会贵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也在这个小小的水文站里一天天孕育长大。如今那里已经成了玛多县城的一道独特风景———高原的绿色。
如果你说谢会贵伟大,他会告诉你他很平凡,平凡得和千千万万的水文人一样,而且“做得比我好的大有人在”。
可是我们却说,谢会贵伟大,他的伟大就在于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将平凡做到了极致。
30年,谢会贵用自己的青春在平凡的岗位上为共和国的水文事业默默地奉献着。
黄河为他作证,他将自己的青春奉献给了这里,而他献给这里的又不仅仅是他的青春,还有对黄河的无限热爱。
来源:中国水利报 2007年4月28日